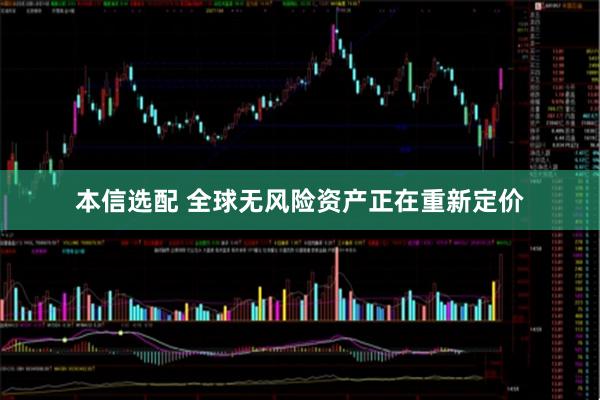
□程实 周烨
2025年下半年,全球经济站在结构重估与风险交汇的关键节点。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政策扰动持续深化,全球经济增长惯性被打断,系统性风险全面显现:贸易壁垒重构全球供需格局,宏观政策工具逼近极限,制度信任机制不断弱化,而长期以来资产价格的高估可能进一步放大市场脆弱性。
主要经济体结构分化
政策不确定性抬升正加剧主要经济体结构分化。美国方面,受政策失序与金融环境偏紧的制约,经济面临增长乏力、政策受限与预期失锚的三重压制,增长动能削弱,内生风险上升。
欧元区虽试图通过财政再扩张稳定经济增长,但受制于结构性低增长与外围环境的扰动,短期内或难突围。而日本经济仍在财政可持续性、促进内需与控制输入性通胀之间寻求平衡,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额外冲击下,政策调节空间或进一步受限。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内部分化趋势增强,高负债国家受制于融资压力与汇率波动,具有人口红利与制度韧性的经济体则可能在全球资本重配中脱颖而出。对于资产配置而言,当前全球市场的焦点已从关注短期变量转向对底层运行机制的评估。美元无风险资产的地位正被重估,高估值高久期资产定价风险抬升。全球资本市场由此进入新一轮寻找锚定的波动周期,资产配置逻辑正在重构。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全球资产定价逻辑转变的过程中,需要警惕市场波动放大与资产定价体系重估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压力。审慎评估优化信用敞口与流动性管理策略,或是穿越周期变局,在风险交汇处稳中求进的关键所在。
新兴市场分化更加显著
2025年下半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面临内外压力的双重叠加。上半年全球金融条件依然偏紧,虽有局部降息预期浮现,但高利率滞后效应正在加速显现,对高负债的新兴市场来说,外汇储备不足、再融资成本高仍是短期金融脆弱性的重要来源。
美国关税政策外溢加剧全球贸易链重构,造成中间品需求与资本转移的地域性收缩,部分制造业转移承接国未能实现产能与基础设施的同步跟进,出现产业空转与外资流出并存局面。地缘政治风险、汇率波动加剧叠加全球对冲情绪升温,使多数新兴经济体在政策上更趋谨慎,货币政策空间与财政扩张能力受限。
下半年,新兴市场将更多依赖内生结构改革与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如东盟、拉美区域合作强化等。在增长路径分化的背景下,具备人口红利、财政纪律与制度稳定性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受到全球资本的青睐。
全球大类资产重估
当前,金融层面的锚定能力正在减弱。主要货币与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明显放大,资本的耐心减弱以及流动速度加快,在金融系统内部构成风险溢价的正反馈机制。汇率成为最早反应的变量,但其波动已难以通过传统宏观逻辑完全覆盖。金融资产的估值体系开始脱离以通胀或利率为核心的定价逻辑,转向更具结构性不确定性的地缘、信用与制度层面考量。
2025年下半年,全球资本流动的路径不再简单服从于利差套利或增长比较,而是在避险逻辑、政策稳定性、制度可信度与资产负债结构等多重维度上进行锚点重估。金融市场表现出高度敏感性,更倾向于在高波动中寻找相对安全区,资本配置的行为函数正发生深刻变化。
新兴市场获得结构性利好
长期以来,全球对美国国债的持续需求和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敏感性。而当前财政杠杆的过度透支、货币政策的约束、市场对美国资产定价体系的重估,正在共同推动全球金融体系进入一个“美元相对收缩、避险再锚定”的调整周期。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而言,长期投资者已经开始重新评估美元资产的风险收益比。在这一过程中,非美货币与实物(黄金、瑞郎、日元等)避险资产、其他主要储备货币的配置比重或进一步增加。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金融体系“无风险资产基准”的锚定地位,一旦发生扰动,将通过估值体系、抵押品体系与风险定价体系形成广泛外溢。这一变化意味着,不仅融资成本将整体抬升,资本市场内部也将面临信用等级与流动性预期的重构。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将引发流动性紧缩、风险溢价上行与资产间传导失衡,全球资本市场可能由此陷入新一轮信用紧缩周期,宏观流动性与金融稳定性同步承压。
私人资本与机构资金则加快轮动节奏,在高频数据、政治信号与利差变化间博弈,更倾向于短期套利与事件驱动策略。预计下半年新兴市场仍将面临外部流动性约束,但部分新兴市场的制度可信度与增长稳定性将成为吸引资本的关键变量。新兴市场国家若能维持政策清晰性与增长稳定性,有望在全球资金再配置中获得结构性利好。
拥有较强外汇储备与本币资产市场的国家在人口结构红利与制造业替代效应的支撑下可能成为全球产业链重组与外资布局的首选地带。综合而言,在全球无风险资产锚定结构发生演化的过程中,投资者应警惕市场波动放大与资产定价体系重估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压力。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烨系工银国际宏观分析师)
天天盈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